

施蛰存轶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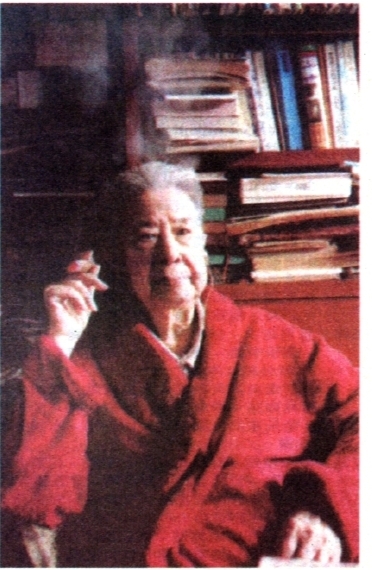
施蛰存教授在愚园路寓所(1993年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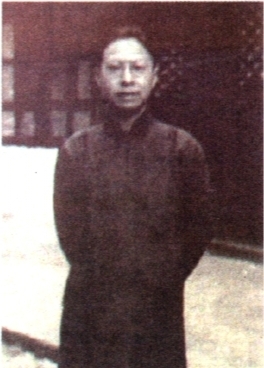
施蛰存教授在昆明云南大学任教期间留影(1938年)

在第二届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颁奖仪式上,原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给施蛰存教授颁奖(1993年)
见习记者 陈佳欣
有人说他是“文坛巨星,学界泰斗”,有人说他是“百科全书式的权威”,学融中西、道贯古今的施蛰存的确受之无愧。他一生的学术成就被称作“北山四窗”:东方文学研究的“东窗”,西方文学翻译之“西窗”,文学创作谓之“南窗”,金石碑版研究 开启了“南窗”。而且,除了“大学家”的身份之外,他独 特的人格魅力同样令人敬重。当我们俯拾那些逸事旧闻,或许会不经意地窥见他人格的“四窗”:浪漫、仗义、风趣、率真。
施蛰存简介
施蛰存:(1905年12月3日——2003年11月19日),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、文学翻译家、学者。原名施青萍,笔名青萍、安华、薛蕙、李万鹤、陈蔚、舍之、北山等。1905年冬出生于杭州,1912年春随父母迁居松江。从江苏省 立第三中学(今松江二中)毕业后考入杭州之江大学,后来又转入上海大学、大同大学、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习。20世纪30年代,施蛰存在中国第一次运用心理分析创作小说《鸠摩罗什》、《将军的头》等,被海内外学术界誉为“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先驱者”。由他主编的《现代》杂志,引进现代主义思潮,推崇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,在当时影响广泛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曾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、厦门大学、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,并从事散文创作和欧洲文学翻译。1952年以后他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,致力于古典文学和碑版文物的研究工作。鉴于其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贡献,1993年施蛰存被授予“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”。
松江“文学工场四剑客”
1927年“四·一二”政变爆发,广州、武汉、南京、上海各地,国民党右翼分子纠集了一群气焰嚣张的打手,突袭了国民党左翼党部和中共地下党部,无数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被逮捕和枪杀,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在城市的上空。施蛰存、戴望舒和杜衡纷纷撤离震旦大学校舍,各自回家暂避。岂料当戴望舒和杜衡回到杭州老家时,却发现那里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猖狂,杭州城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。于是他们相约来到施蛰存家中避难。
其实施蛰存打从学校回到松江家里之后也是闷闷不乐,总嫌一个人看书怪孤单的,连个可以一块切磋讨论的同伴都没有,这时见到昔日同窗顿觉喜出望外,立即把家里的小厢楼收拾一新,请两位朋友搬来同住,还提议把这里当作“文学工场”。三个人于是闭门不出,在静静的小厢楼里读书闲谈,翻译外国文学,没几个月,夏多布里昂的《少女之誓》、海涅的《还乡集》、显尼志勒的《倍尔达·迦兰夫人》的中译本就在三人手中诞生了。
而“文学工场”第四位成员的加盟就颇有些戏剧性了。1928年初,戴望舒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一封信。施蛰存侧身张望了一下信封,随口问道:“冯雪峰这名字听上去挺熟的,《春的歌集》是不是他写的呀?”
“没错,就是他。七月份我不是正巧在北京吗,我就是那会儿认识他的。这个人特别有意思,跟他聊起我们三人在你家小厢楼上办‘文学工场’,他就直呼我们仨‘松江三剑客’。”戴望舒边说边展开信纸,不禁笑起来:“哎呀,难不成我们要组成‘四剑客’啦,冯雪峰在信上说他打算南下,想在松江歇歇脚,蛰存你看怎么样?”
施蛰存满口答应:“欢迎欢迎,我马上在小楼上新安一张床,随时恭候他大驾光临。”说着又催促戴望舒给对方复信确认。
可过了几个星期,冯雪峰却回信说,南归计划受阻了,原因是他在北京结识了一位风尘女子,两人情投意合,决定携手远走高飞。要为这位红颜知己赎身得花400块钱,这令他这个穷书生十分犯难,无奈之下只得请求“三剑客”慷慨解囊以解他燃眉之急。读罢这封信,戴望舒早已目瞪口呆,脸涨得通红,别过头悄悄打量施蛰存的反应,只见他面无难色且不假思索就朗声说道:“冯雪峰对这个姑娘如此情有独钟,我看她肯定不同寻常,说不定还是红拂女、柳如是那样的人物,我们怎么能棒打鸳鸯呢?”说罢他就把自己在中学任教时积攒下来的200块钱取了出来,要知道他当时一个月工资也不过70多块钱。刚才还神色尴尬的戴望舒和杜衡心头那股“浪漫主义精神”仿佛一下子被施蛰存点燃了,两个人也想方设法凑出了200块钱,一起拿到银行汇给了冯雪峰。
几天后,得知冯雪峰已经顺利抵沪,三人兴冲冲地乘早车赶到上海接他。可出乎众人意料的是,迎面走来的冯雪峰一个人提着行李,身边没有女眷相伴,施蛰存见状迫不及待地上前问他:“那位姑娘没有来吗?是怕我不收留吗?”
冯雪峰望着施蛰存严肃的表情,一下子哭笑不得:“哎呀,哪会有姑娘愿意跟我走啊?我其实是想帮几个朋友离开北京筹一笔钱,当时只是一时兴起,就随口编了个浪漫故事,哪里知道你们一直记挂在心上……真不好意思,和大家开了个这么大的玩笑。”
“哦,原来如此啊。”施蛰存不怒反笑,“冯雪峰啊,我只知道你写诗有一手,想不到你还挺有小说创作的天赋嘛。”
“对呀,我的小说就叫《云间三剑客解救京城茶花女》,听上去还蛮有传奇色彩的吧。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早已笑作一团。
回到施宅小厢楼里,四人重整旗鼓投入到著书译文中。这个小小的“文学工场”前后仅仅存在一年,却是我国现代派诗歌、新感觉派心理小说的主要诞生地,也是施蛰存文学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个驿站。
施蛰存与沈从文交谊拾趣
四腮鲈鱼酬知己
在1927年白色恐怖威胁下被迫南下的并不只有冯雪峰一个人。沈从文、姚蓬子、丁玲、胡也频等进步青年都在那个时期先后来到上海。经冯雪峰介绍,施蛰存与他们渐渐熟识起来,而他与沈从文相知特别深。1929年10月,施蛰存与陈慧华在家乡松江举行婚礼,这些文艺界的朋友纷纷从上海赶来贺喜。沈从文手捧一卷装裱精致的横幅,笑吟吟地恭贺好友新婚之喜:“蛰存,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,我代表丁玲、胡也频为你写了一副贺词,打开看看吧。”施蛰存连忙展开横幅,凝神端详,鹅黄洒金笺的纸面上沈从文的草书清逸潇洒:“多福多寿多男女”。这句贺词出自“华封三祝”,原句应是“多男子”,沈从文为求祝福更周全,就颇为贴心地小改一字,施蛰存见状不由会心一笑。“大家费心了,赶快里边请。待会我要隆重推出一道美味佳肴,只有在我们松江才吃得到。”
这到底是道什么菜?满座宾客正在猜测,一个热气腾腾的铜锅被摆上了桌,顿时鲜香四溢。“这就是我们松江名产四腮鲈鱼,是十月新鲜上市的呢,大家别客气,赶快来尝尝。”
呷一口醇厚浓滑的鲜汤,嚼一块嫩滑剔透的鱼肉,再在杯中斟满美酒,宾客尽情享受着四腮鲈鱼的美味。“今日薄暮,举网得鱼,巨口细鳞,状如松江之鲈。”在一片微醺的气息中,沈从文竟摇头晃脑地吟诵起《后赤壁赋》来。“我今天总算尝到了让曹孟德和苏东坡如痴如醉的松江四腮鲈鱼,果然名不虚传呀。”这一席酒,大家都吃得谈笑风生,久久不愿散去。饮至晚上九时,才分乘人力车到火车站,搭十点钟的杭沪夜车回到上海。
地摊铺上觅宝贝
1937年,两人又在昆明重新聚首,对文物颇有研究的沈从文就理所当然担负起了逛夜市、淘古董的“参谋”。昆明有一条福照街,每晚有夜市,摆了五六十个地摊。摊主都是拾荒收旧者,每个地摊都点了一盏电石灯,绿色的火焰照得地面亮亮的。
这些地摊上的货物大多是家用器物。电料、五金零件、衣服之类,他们看一眼就走过,但沈从文“慧眼识珠”,常有意外的收获。有一次,他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,瓷质洁白,很薄,画着一匹青花奔马。他说:“这是康熙青花瓷,一定有八个一套,名为‘八骏图’”。原来他专收古瓷,古瓷之中,又专收盆子碟子。在北平家里,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。
有一天晚上,他们在一堆旧衣服中发现两方绣件,好像是从朝衣补褂上拆下来的。沈从文立刻劝施蛰存买下:“值得买。外国妇女最喜欢中国绣件,拿回去做壁挂,你买下这两块,将来回上海去准可以销洋庄。”果不其然,施蛰存后来把绣件送给了林同济夫人(她是位美国人)做茶几垫子,特别受欢迎。
在福照街夜市上,两人最爱去的就是古董摊子。这些地摊上,常有古书、旧书、文房用品、玉器、漆器,有时还可以发现琥珀、玛瑙,或大理石的雕件。巧合的是,两人都对缅刀和缅盒情有独钟。沈从文未来昆明之前,施蛰存已买到一个小缅盒,朱漆细花,共三格,和江南古墓中出土的六朝奁具一样,沈从文见了把玩不已,对施蛰存的眼光赞不绝口。施蛰存就爽快地答应沈从文下次陪他再去福照街“寻宝”,一定要找个一样的缅盒回来。从松江到昆明,施蛰存和沈从文虽不可谓亲密无间,却有着至交间难能可贵的默契。
江苏路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仅提供技术服务支持, 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版权归属发布媒体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