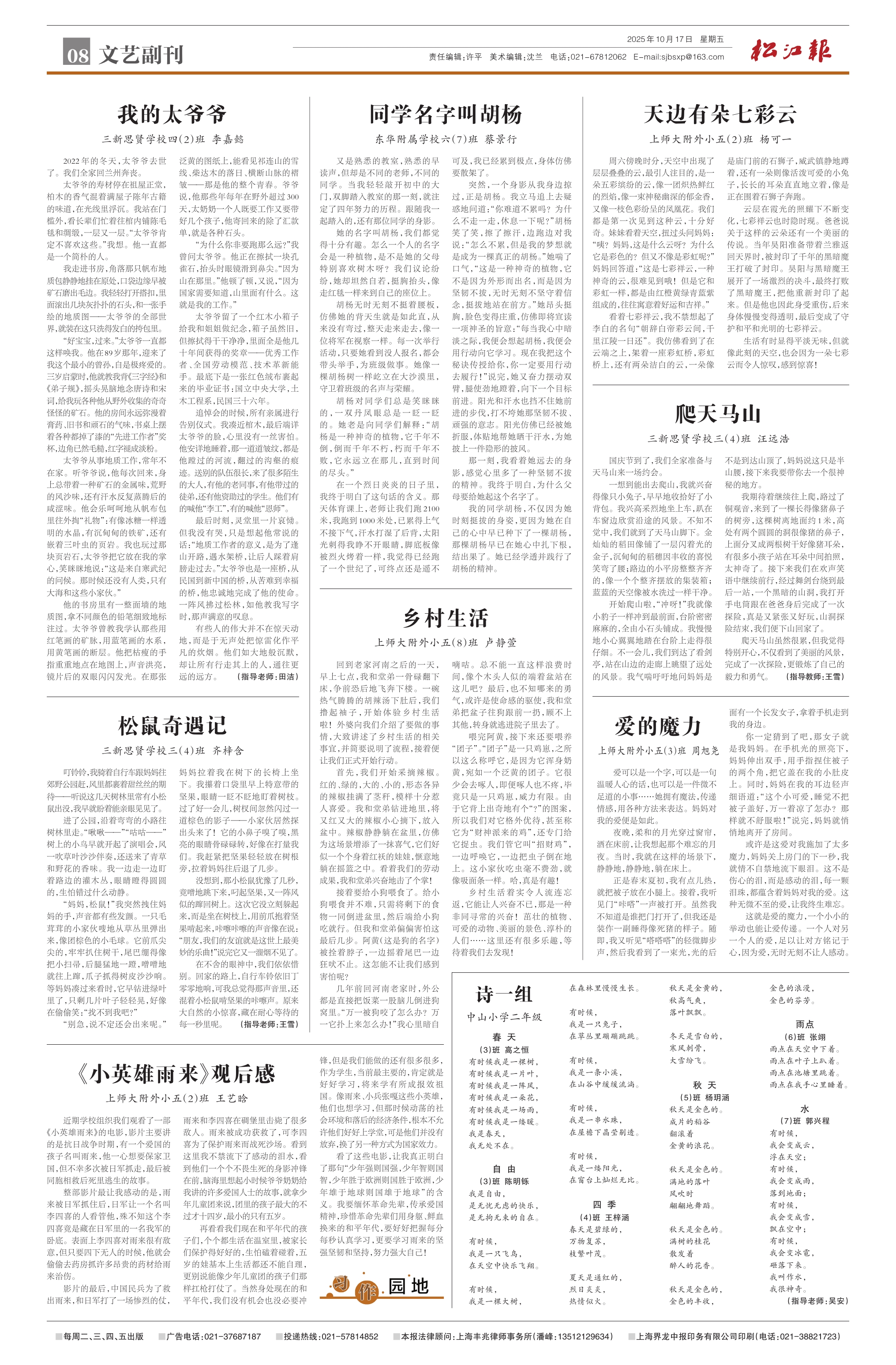

我的太爷爷
三新思贤学校四(2)班 李嘉懿
2022年的冬天,太爷爷去世了。我们全家回兰州奔丧。
太爷爷的寿材停在祖屋正堂,柏木的香气混着满屋子陈年古籍的味道,在光线里浮沉。我站在门槛外,看长辈们忙着往棺内铺陈毛毯和绸缎,一层又一层。“太爷爷肯定不喜欢这些。”我想。他一直都是一个简朴的人。
我走进书房,角落那只帆布地质包静静地挂在原处,口袋边缘早被矿石磨出毛边。我轻轻打开搭扣,里面滚出几块灰扑扑的石头,和一张手绘的地质图——太爷爷的全部世界,就装在这只洗得发白的挎包里。
“好宝宝,过来。”太爷爷一直都这样唤我。他在89岁那年,迎来了我这个最小的曾孙,自是极疼爱的。三岁启蒙时,他就教我背《三字经》和《弟子规》,摇头晃脑地念唐诗和宋词,给我玩各种他从野外收集的奇奇怪怪的矿石。他的房间永远弥漫着膏药、旧书和顽石的气味,书桌上摆着各种都掉了漆的“先进工作者”奖杯,边角已然毛糙,红字褪成淡粉。
太爷爷从事地质工作,常年不在家。听爷爷说,他每次回来,身上总带着一种矿石的金属味,荒野的风沙味,还有汗水反复蒸腾后的咸涩味。他会乐呵呵地从帆布包里往外掏“礼物”:有像冰糖一样透明的水晶,有沉甸甸的铁矿,还有嵌着三叶虫的页岩。我也玩过那块页岩石,太爷爷把它放在我的掌心,笑眯眯地说:“这是来自寒武纪的问候。那时候还没有人类,只有大海和这些小家伙。”
他的书房里有一整面墙的地质图,拿不同颜色的铅笔细致地标注过。太爷爷曾教我学认那些用红笔画的矿脉,用蓝笔画的水系,用黄笔画的断层。他把枯瘦的手指重重地点在地图上,声音洪亮,镜片后的双眼闪闪发光。在那张泛黄的图纸上,能看见祁连山的雪线、柴达木的落日、横断山脉的褶皱——那是他的整个青春。爷爷说,他那些年每年在野外超过300天,太奶奶一个人既要工作又要带好几个孩子,他寄回来的除了汇款单,就是各种石头。
“为什么你非要跑那么远?”我曾问太爷爷。他正在擦拭一块孔雀石,抬头时眼镜滑到鼻尖。“因为山在那里。”他顿了顿,又说,“因为国家需要知道,山里面有什么。这就是我的工作。”
太爷爷留了一个红木小箱子给我和姐姐做纪念,箱子虽然旧,但擦拭得干干净净,里面全是他几十年间获得的奖章——优秀工作者、全国劳动模范、技术革新能手。最底下是一张红色绒布裹起来的毕业证书:国立中央大学,土木工程系,民国三十六年。
追悼会的时候,所有亲属进行告别仪式。我凑近棺木,最后端详太爷爷的脸,心里没有一丝害怕。他安详地睡着,那一道道皱纹,都是他蹚过的河流,翻过的沟壑的痕迹。送别的队伍很长,来了很多陌生的大人,有他的老同事,有他带过的徒弟,还有他资助过的学生。他们有的喊他“李工”,有的喊他“恩师”。
最后时刻,灵堂里一片哀恸。但我没有哭,只是想起他常说的话:“地质工作者的意义,是为了逢山开路,遇水架桥,让后人踩着肩膀走过去。”太爷爷也是一座桥,从民国到新中国的桥,从苦难到幸福的桥,他忠诚地完成了他的使命。一阵风拂过松林,如他教我写字时,那声满意的叹息。
有些人的伟大并不在惊天动地,而是于无声处把惊雷化作平凡的炊烟。他们如大地般沉默,却让所有行走其上的人,通往更远的远方。
(指导老师:田洁)
江苏路特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仅提供技术服务支持, 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版权归属发布媒体

